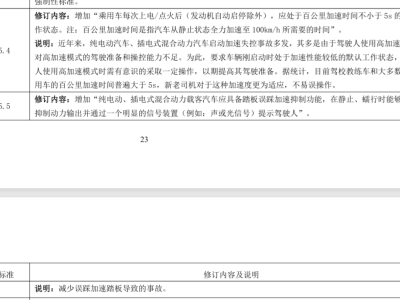當“把飛機放進量子計算機里吹風”這樣的表述從科幻想象變為現實,全球科技領域都為之側目。我國科研團隊利用“本源悟空”超導量子計算機,成功完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量子計算流體動力學(QCFD)仿真,這項成果涵蓋一億網格、百萬時間步以及全三維湍流場,且一次運算耗時不到傳統超級計算機的千分之一,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傳統航空設計領域,驗證新機翼是否省油是一項關鍵工作。設計師通常會先在計算機中進行虛擬風測試,觀察氣流在翼面的情況,比如是否會出現打旋、分離以及制造阻力等現象,這一流程被稱為計算流體動力學(CFD)。過去五十年,工程師依靠經典超級計算機求解納維 - 斯托克斯方程。網格劃分越精細,得到的結果就越真實,但所需的算力也會呈指數級增長。以一架全尺寸客機為例,進行億級網格仿真,即便動用上萬塊CPU,也需要晝夜不停地運行數周時間。正因如此,世界各大航空城至今仍保留著巨型風洞,用于完成計算機難以處理的任務。
量子計算的出現,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從宏觀角度看,流體是連續的,但從微觀層面而言,它是無數分子碰撞的統計結果。而量子比特在處理“統計游戲”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它可以將空氣粒子視為概率云,通過薛定諤方程直接演化其分布,無需像傳統方法那樣一格一格地計算有限體積。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困難重重。流體方程具有強非線性,邊界條件復雜,還需要處理不可壓縮約束。當量子線路深度增加時,噪聲會呈指數級膨脹。過去十年,全球多個團隊進行了嘗試,但大多局限于幾千網格、二維層流的“玩具模型”。
“本源悟空”此次取得的突破,關鍵在于“混合 - 壓縮 - 糾錯”三招組合拳。第一招是混合算法,研究團隊將大渦模擬(LES)的思想引入量子線路。先利用經典網格過濾出超大渦團,再把小尺度脈動“打包”成量子態,讓量子比特負責演化最容易失控的湍流耗散區,經典CPU則負責處理剩余的骨架場。雙方每完成一個時間步的計算就進行一次數據交互,這樣既節省了量子資源,又保證了計算精度。第二招是壓縮線路,通過引入“變分量子生成網絡”(VQGAN),將原本需要上萬門的線路壓縮到幾百門,線路深度降低一個量級,噪聲累積得到有效控制。第三招是糾錯層,利用“悟空”72比特芯片的并行讀出能力,實時監測比特翻轉情況。一旦超出閾值,就動態重算,只修復出現問題的部分,避免整體重新計算。三招協同作用,使得一億網格、百萬步的“夢幻仿真”在量子計算機中成功運行,全程耗時不到4小時,而同等精度的經典超級計算機預估需要運行3000小時。
速度提升了,結果的可靠性如何呢?研究團隊進行了三重交叉驗證。首先,將量子計算結果與歐洲某經典超級計算機中心的高精度數據進行對比,壓力分布誤差在1%以內。其次,使用同一套算法在經典計算機上運行“降維版”程序,得到的升力、阻力曲線幾乎與量子計算結果重合。最后,將仿真得到的油流譜貼在真實風洞模型上進行可視化,分離線位置與實驗照片幾乎無法用肉眼區分差異。三重驗證均通過,業內才認可這是一項“真正有用的量子CFD”成果,而非簡單的“玩具加速”。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風洞即將退出歷史舞臺呢?目前來看,還為時尚早。量子CFD目前更像是“特種突擊隊”,在遇到極其復雜、高度敏感且需要反復迭代的場景時,它能發揮關鍵作用。而在日常大量常規型號的驗證工作中,經典CFD加速卡仍然具有更高的性價比。更重要的是,當前量子芯片還處于“含噪聲中等規模”(NISQ)時代,比特數、相干時間、門保真度等都存在一定限制。即使進行更大規模的仿真,也需要依靠混合框架借助經典計算機的能力。也就是說,風洞、超級計算機和量子計算機并非相互取代的關系,而是共同構成了“航空設計三件套”:風洞提供真實數據,超級計算機拓展計算廣度,量子計算機挖掘計算深度。
量子CFD的應用前景遠不止于航空領域。高速列車穿越隧道時產生的壓力波、火箭級間分離時的瞬態渦流,甚至是血液在心臟瓣膜周圍的湍流,這些場景都對網格分辨率有著極高的要求。一旦量子比特規模突破百萬,相干時間突破秒級,這些傳統計算方法難以處理的場景都有可能被攻克。更令人期待的是“反設計”的可能性,傳統設計流程是先繪制外形再計算性能,而未來量子計算機強大后,可以直接以“最低阻力”“最小噪聲”為目標,反向演化出最優曲面,讓算法為人類“創造”出自然界中完美的形狀。
對于普通人來說,或許無需深入理解量子門、哈密頓量、變分循環等復雜的科學概念。只需知道,空氣不再僅僅是在風洞中呼嘯而過,它也可以在量子世界里化作一簇概率云,在芯片上悄然演化。未來,我們乘坐的飛機、高鐵甚至私家車,其外形或許就誕生于這樣一場“無聲的量子風暴”。科學的前沿看似遙遠,卻終將在某一天化作我們窗外掠過的優美流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