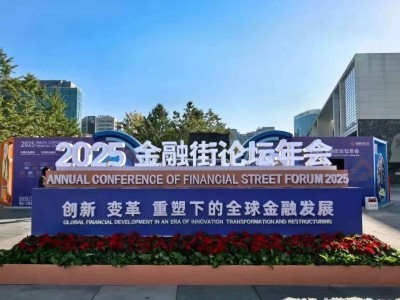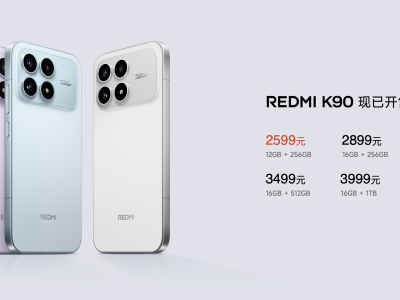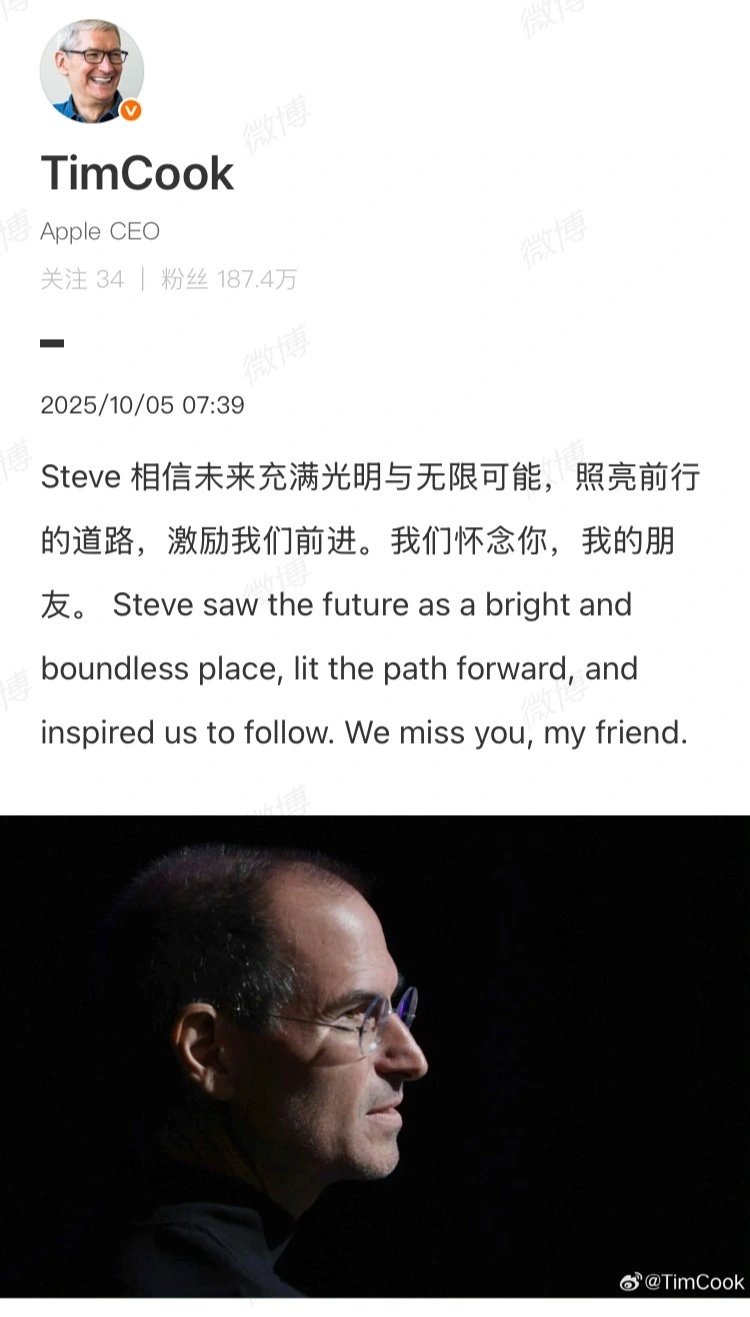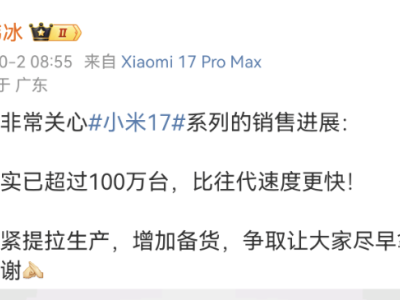當鄭國霖身著龍袍在西安某景區說出“陛下,您還記得當年的大唐嗎?”時,周圍游客的歡呼聲瞬間沸騰。這位因飾演李世民而深入人心的演員,如今以景區NPC的新身份引發關注——他騎著摩托車載“秦始皇”穿行的視頻在短視頻平臺播放量破億,相關話題累計曝光量輕松過億。與此同時,廣東某景區內,“石榴姐”苑瓊丹穿著古裝演唱粵語老歌,臺下游客舉著手機瘋狂拍攝;70歲的寇振海揮動鞭子重現《情深深雨蒙蒙》經典場景,讓中老年游客直呼“青春回來了”。這些“過氣明星在景區打工”的畫面持續刷屏,輿論場迅速分化:有人感嘆“明星淪落”,更多人則認為“靠本事吃飯不丟人”。
這場現象的背后,是影視行業寒冬、文旅產業升級與大眾消費需求變遷的三重碰撞。表面看是明星“再就業”,實則是兩個行業結構性矛盾的臨時解法。當前影視圈已進入“流量至上”時代,開機項目銳減,資本集中涌向頭部藝人,中腰部演員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35歲的演員史元庭透露,2025年上半年他僅有4天戲可拍;鄭國霖也坦言,因不愿重復同類角色且機會減少,陷入事業低谷。這些演員雖面臨“結構性失業”,但顏值、演技與國民度仍在,尤其是經典角色帶來的“情懷濾鏡”,成為他們轉型的隱形資產。當影視圈無法消化這些產能,他們必須尋找新出口。
景區端的困境同樣迫切。傳統“門票經濟”已難以為繼,游客不再滿足于“下車拍照”的觀光模式,轉而追求互動性強、情緒價值高的體驗式消費。然而,景區在營銷上屢屢碰壁:短視頻平臺投放廣告效果有限,邀請網紅探店成本高昂且效果參差——一個百萬粉絲網紅的推廣費動輒數十萬,轉化率卻難以保證。就在景區為流量發愁時,他們發現影視圈“待業”的明星恰是破局關鍵:明星自帶國民度與話題性,近距離互動能制造天然情緒價值,堪稱為景區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
這種雙向奔赴迅速催生新業態。景區提供場地與客流,明星貢獻演技與情懷,雙方各取所需。鄭國霖直言:“景區需要內容創新,而我需要一個舞臺。”對景區而言,明星NPC不僅是“打工者”,更是高回報率的營銷工具。其“反差感”本身即是流量密碼——當觀眾印象中“高高在上”的明星突然出現在景區互動,這種身份落差極易引發討論。苑瓊丹唱老歌、馬景濤“咆哮”表演等場景被游客拍攝上傳后,往往能引發自發傳播,效果遠超花錢買廣告。某景區負責人透露,邀請古裝明星駐場后,門票銷量一周暴漲150%,相關話題閱讀量破億,停車場甚至需加派人手。
更關鍵的是,明星NPC的成本遠低于頂流代言費,部分“過氣明星”的出場費甚至低于頭部網紅,但曝光量與轉化效果卻天差地別。然而,這種模式也暗藏風險:明星合約到期后,景區可能陷入“明星依賴癥”——請明星時門庭若市,明星離開后門可羅雀。部分景區已因此遭受重創,本質是將核心競爭力建立在外部IP上,而非自身內容價值。
為避免“曇花一現”,部分景區開始探索長期轉型路徑。第一種模式是“IP本土化”:某少數民族景區邀請明星穿民族服飾當NPC,同時包裝素人員工為“網紅導游”。這些本土導游的號召力逐漸不輸二線明星,且成本低、忠誠度高,還能深度解讀文化,形成景區自有IP矩陣。第二種模式是“內容深度綁定”:景區邀請明星參與短視頻劇本創作與角色設計,一條由明星共創的視頻播放量破千萬,明星標簽與景區內容深度融合,即使明星離開,內容資產仍能持續吸引游客。第三種模式是“情懷場景化”:某武俠主題景區將明星經典角色改編為沉浸式劇本殺,游客可扮演角色與“明星NPC”互動。明星離開后,劇本殺場景被保留為核心項目,持續產生吸引力。
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核心邏輯:流量是快變量,運營是慢變量;明星是外驅力,內容是內驅力。能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景區,才能將短期熱度轉化為長期品牌價值。否則,明星終將成為“一次性流量工具”,無法拯救景區命運。對明星而言,這是放下身段后的“降維打擊”;對景區而言,這是找對方法后的“事半功倍”;對游客而言,這是用低成本獲得的“情緒滿足”。但當熱鬧褪去,真正能留住游客的,始終是景區自身的內容精彩度、體驗獨特性與文化深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