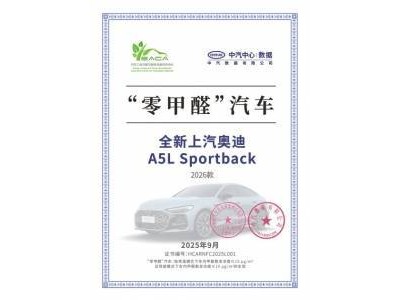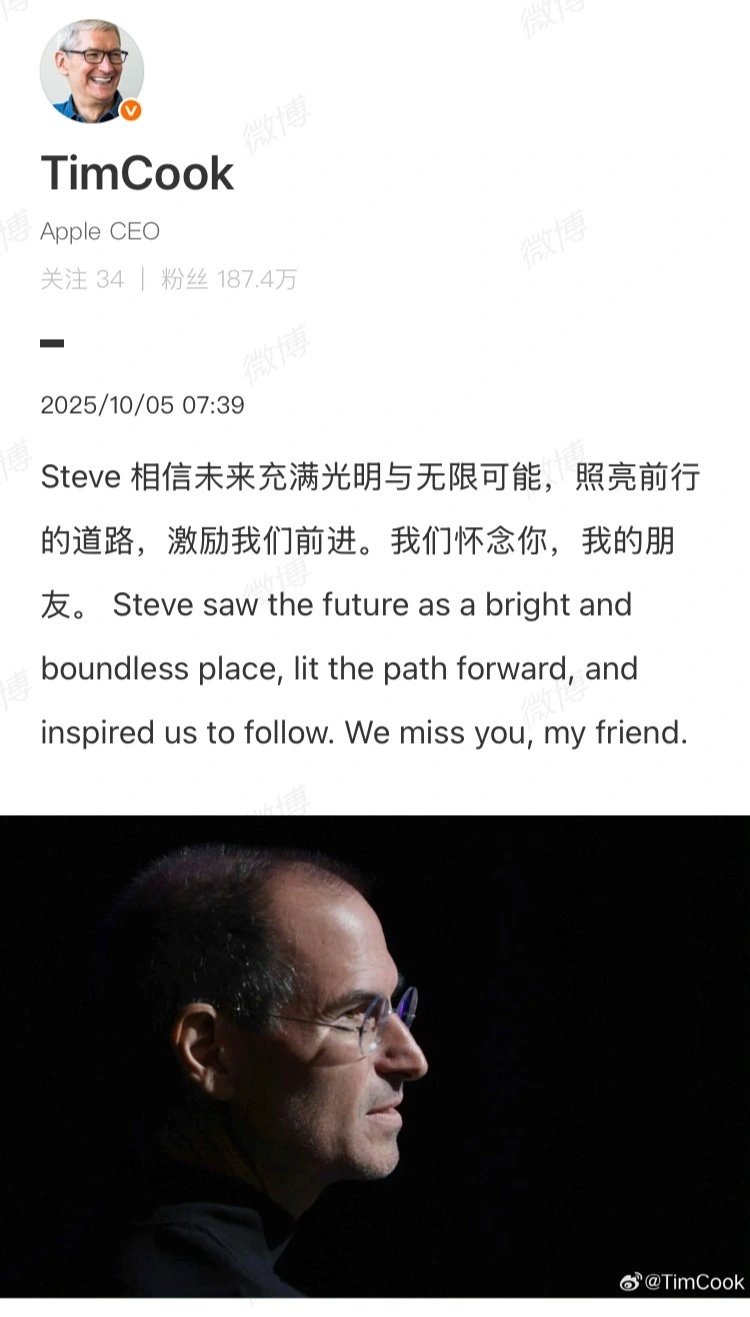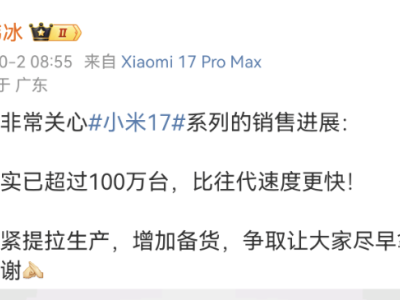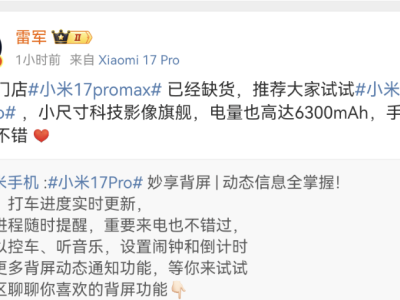清晨六點的喀什,天色尚未破曉。手機屏幕亮起,是母親發來的新消息——幾張天水老家的照片,畫面里是剛鋪完水泥的巷子,隔壁王叔家新蓋的三層小樓,還有巷口那棵依舊挺立的老槐樹。只是樹蔭下的青石板上,當年我們刻下的字跡早已模糊難辨。
六年來,喀什的風沙早已融入呼吸,羊肉抓飯的香氣成了日常,可每當夜深人靜,總忍不住想起天水老家那輪濕潤的月亮。母親的拍照技術依舊笨拙,照片總是歪斜模糊,但每一張都被我反復放大,從巷頭的老井到巷尾的柴垛,從春日的柳芽到秋收的麥垛,她用這種方式,替我記錄著故鄉的每一次呼吸。
可照片終究留不住老屋院里的桂花香,拍不出雨后青石板路的反光,更捕捉不到鄰居站在巷口喊“回家吃飯”的鄉音。那些被歲月浸透的細節,成了手機屏幕永遠無法承載的鄉愁。
記憶里的夏天,總在老家的院子里鋪開。祖母搖著蒲扇,指著月亮講嫦娥的故事,說玉兔在月宮里搗藥。我仰著頭看,直到脖子發酸,才相信那些閃爍的星星都是神仙的眼睛。后來在學校學了天文,才知道那些不過是隕石和星云,可每當抬頭看月亮,依然覺得它比喀什的更圓更亮——或許是因為戈壁灘的夜空太遼闊,襯得月亮太過孤單;又或許,是看月亮的人,心里裝著太重的思念。
母親在電話里說,老家要拆遷了,整個片區都要改造。她特意拍下每一處即將消失的角落:我們一起乘涼的老院子,我第一次學騎車時撞壞的墻角,還有巷口那家開了三十年的雜貨鋪。她說:“等你回來,可能連路都認不得了。”我嘴上硬氣:“不會的,故鄉在心里,永遠都認得。”可掛斷電話后,卻對著窗外的風沙發了很久的呆——三年沒回去,那些熟悉的風景,是否真的只能活在記憶里?
父親退休后,視頻通話的次數多了,可每次都說不了幾句就匆匆掛斷。我知道,他只是不習慣對著手機表達牽掛。就像我,每次掛斷視頻后,總要對著窗外的夜色發很久的呆,仿佛這樣就能離故鄉更近一點。
在喀什,我結識了許多從內地來的朋友。聚在一起時,總會聊起各自的故鄉:四川的火鍋、陜西的羊肉泡饃、河南的燴面……說著說著,聲音就低了下去。原來,每個異鄉人的心里,都藏著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蘇軾說:“此心安處是吾鄉。”可心安何處?在喀什,我學會了幾句當地方言,結交了新的朋友,可每當夜深人靜,聽見窗外呼嘯的風聲,總會想起天水老家院子里那棵在風中沙沙作響的梧桐。或許,故鄉從來不是某個具體的地點,而是母親的照片、父親的沉默、還有我們永遠改不掉的鄉音。
天快亮了,喀什的朝陽即將升起。而此刻的天水,月亮應該還掛在天上。我給母親發了消息:“今年過年,一定回家。”她秒回:“好,媽把你房間的被子都曬好了。”
想對每一個在異鄉的人說:找個時間,回故鄉看看吧。不是匆匆路過,而是認真地住上幾天,走走兒時走過的路,看看多年未看的月亮。因為有些風景,會消失;有些人,正在老去;而有些思念,需要親自回去化解。
無論你身在何處,愿今夜都有一輪明月,照亮你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