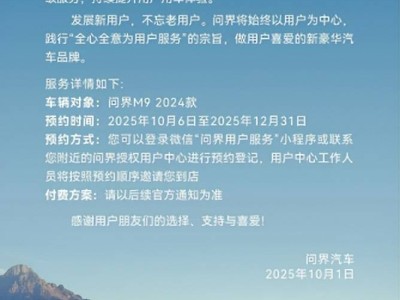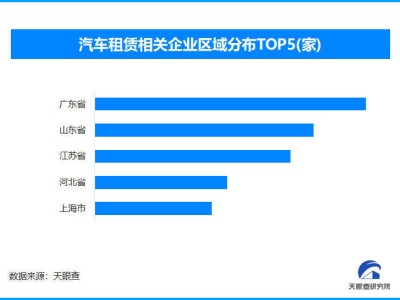青海冷湖的夜空下,裹著兩層沖鋒衣的天文觀測者蹲在望遠鏡旁,原本為拍攝獵戶座星云而來,卻意外邂逅了一場顛覆認知的奇景——墨色絲絨般的夜幕中,十幾道銀藍色光痕從天鵝座方向劃過,它們并非轉瞬即逝的流星,而是如被驚擾的魚群般,拖著細碎光斑“游動”于大氣層邊緣,尾跡中還散落著淡藍色熒光,仿佛海水里的浮游生物隨魚群散開。
同行的行星科學家老鄭當場愣住,保溫杯差點脫手。他們反復回放記錄儀,發現這些“飛魚”的軌跡完全違背已知規律——既非彗星碎片,也非衛星殘骸。其速度隨恒星風強度變化,快時達每秒40公里,慢時如乘氣流盤旋,甚至兩次出現“折返”弧度,仿佛在躲避無形屏障。
查閱歷史資料后,觀測團隊發現類似現象早有記錄。1978年,NASA宇航員在空間站首次觀測到此類光團,將其命名為“大氣異常光團”,但僅記錄3次后便無后續。2015年,歐洲南方天文臺推測這些光團是太陽系邊緣的冰晶顆粒被太陽風推至地球附近形成,但2023年加州理工的新研究通過衛星光譜分析發現,光團成分含硅基化合物,且釋放微弱電磁信號,徹底推翻了冰晶假說。
老鄭提出的“恒星風生存”假說引發討論。他認為,若這些“飛魚”是未知宇宙物質,其運動軌跡恰似候鳥捕捉氣流——它們會順著恒星風調整速度,甚至通過表面結構“吸收”帶電粒子。這一說法雖似科幻,但國際空間站的粒子探測器曾檢測到,類似現象出現時,周圍太陽風粒子濃度驟降17%,仿佛有“無形之手”將粒子“抓走”。
為驗證猜想,團隊整理近十年觀測數據,發現更多關聯:2018年智利觀測站記錄的“飛魚”尾跡僅今年長度的三分之一,當時太陽活動處于極小期;2021年太陽風暴爆發時,澳大利亞天文愛好者拍到三十余只“飛魚”成群掠過,尾跡熒光強度是平時的兩倍。這表明其出現與恒星風強度密切相關,但為何太陽風極強時卻無蹤影?
更離奇的線索來自1969年阿波羅12號的任務記錄。宇航員在月球背陽面短暫捕捉到類似光痕,當時他們以為是登月艙推進器殘留氣體,但后續分析顯示,該區域不可能受地球大氣影響,且太陽風強度處于中等水平,既無耀斑爆發,也無冕洞出現。這些“飛魚”為何會出現在月球表面?
傳統流體力學模型無法解釋“飛魚”的穩定形態——按常規計算,它們本應在大氣層邊緣被撕碎,但實際觀測中,它們不僅保持完整,甚至會分裂成更小的“魚苗”。老鄭嘗試用等離子體物理模型模擬,發現若表面包裹帶電粒子形成的“保護膜”,則可在高速運動中抵抗大氣摩擦,而恒星風恰好能為“保護膜”補充能量。
實驗室實驗進一步支持這一猜想。研究人員用等離子體發生器模擬恒星風,以硅基材料制作“飛魚”模型,發現當等離子體流強度達標時,模型表面形成微弱磁場,且運動軌跡與真實觀測的“飛魚”相似度達60%。但新問題隨之而來:自然界中如何形成如此規整的硅基結構?是否暗示某種未知宇宙生命形態?
觀測團隊還發現,2018年與2021年“飛魚”出現時間,與金牛座流星雨峰值時間相差不足24小時。若它們與流星體同源,為何成分與運動方式截然不同?老鄭查閱資料后指出,流星雨母體彗星的軌道附近,恰好存在被恒星風包裹的塵埃云——這些“飛魚”是否從塵埃云中“孵化”而出?
目前,團隊正籌備前往西藏納木錯觀測站,那里海拔更高、大氣更透明,或能捕捉到更清晰的“飛魚”細節。老鄭曾指著銀河感慨:“人類對宇宙的了解,可能還不如這些‘飛魚’對恒星風的了解多。”或許,當某天我們真正解開“飛魚”之謎時,對恒星風、對太陽系邊緣的認知,將迎來一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