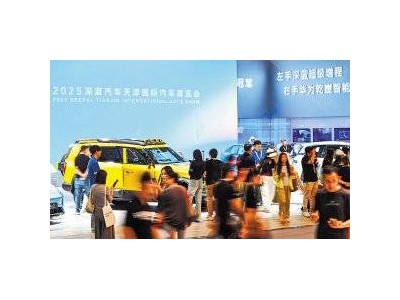當八馬茶業頭頂“高端中國茶第一股”的光環登陸港交所時,資本市場曾為其描繪出一幅高增長的藍圖。然而,這場持續13年的IPO長跑最終以尷尬收場——上市僅10個交易日,股價便跌破50港元發行價,最低觸及49.22港元,市值較峰值蒸發超40億港元。這場資本與茶產業的碰撞,再次暴露出傳統行業與現代金融體系之間的深層矛盾。
八馬茶業的業績轉折堪稱斷崖式。2024年營收增速從2023年的16.72%驟降至0.99%,2025年上半年更出現4.2%的同比下滑,凈利潤同比降幅達17.8%。支撐其擴張的加盟商體系同步顯現疲態:2024年凈增加加盟商數量較2023年減少119家,2025年上半年加盟商總數較2024年底凈減少24家,流失總數已超300家。這種收縮直接導致門店擴張速度放緩,2025年上半年新增加盟店數量不足2023年同期的五分之一。
H股全流通計劃成為壓垮股價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司擬將3193.31萬股內資股轉換為H股,流通股數量將激增60%。在港股市場流動性持續收緊的背景下,這一計劃被解讀為原始股東集中退出的信號。資金流向數據印證了市場擔憂:截至11月11日,該股20日凈流出金額達7746.36萬元,呈現持續拋售態勢。
這種困境并非孤例。早在2023年12月上市的“普洱茶第一股”瀾滄古茶,股價已較10.7港元發行價跌去超70%,近期更創下3港元以下的歷史新低。其2025年中期業績顯示,營收同比下滑38.8%,由盈轉虧2894.6萬元。兩家頭部茶企的集體遇冷,折射出資本市場對傳統茶產業的審慎態度。
茶葉的農產品屬性與資本要求的標準化背道而馳。產地、氣候、年份和制作工藝的細微差異,使得每片茶葉都成為獨特的非標品。這種特性導致茶企面臨品控難題和成本波動,A股市場對茶企IPO的謹慎態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存貨核算和跌價準備等財務處理難題。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高端茶葉市場前五名市占率僅5.6%,八馬茶業1.7%的份額更凸顯行業分散格局。
資本追逐的“高增長、可復制”模式在茶產業屢屢碰壁。大益茶通過限量配售等金融手段炒作普洱茶價格,最終在市場波動中泡沫破裂;泛茶、昌世等品牌以理財產品形式吸引資金,因無法兌付引發崩盤。這些案例表明,試圖用金融杠桿加速茶產業擴張,本質上是對行業規律的違背——茶葉需要時間沉淀品質,而資本要求快速周轉回報。
八馬茶業的資本化之路充滿戲劇性。從2012年引入IDG、天圖資本等機構謀求A股上市,到新三板掛牌,再到兩次沖擊創業板和主板失敗,最終轉戰港股。其背后站著安踏、新希望、七匹狼等戰略投資者組成的“親家天團”,但即便如此強大的資源網絡,也未能改變二級市場用腳投票的結局。當業績失速、模式遇阻、拋壓來襲時,資本市場的冷酷一面顯露無遺。
這場資本與茶產業的博弈,本質上是兩種時間邏輯的沖突。茶葉生長遵循自然節律,品牌培育需要長期投入,而資本市場要求的是可預期的財務表現和快速擴張能力。八馬茶業的遭遇證明,當傳統行業強行套用資本游戲規則時,既可能扭曲產業本質,也難以滿足金融市場的嚴苛要求。這種矛盾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繼續考驗著中國茶企的資本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