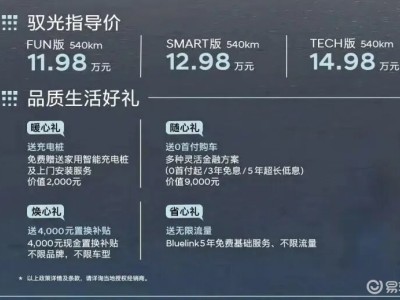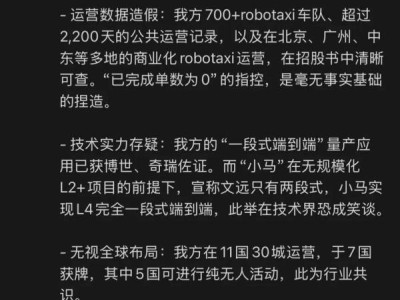第三次調價后,老鋪黃金門店前依然人潮涌動。佛教信徒為求金剛杵而來,普通消費者為投資保值而來,而黃牛則穿梭其中,忙著排隊取號、湊單代購。店門口的告示牌上,“部分款式已售罄”的字樣格外醒目,社交平臺上關于“斷貨”“排隊攻略”“漲價款式”的討論持續刷屏。這種景象,讓人不禁聯想到此前泡泡瑪特引發的全民搶購熱潮,只不過這次的主角換成了客單價五位數的“黃金藝術品”。
消費降級的論調在老鋪黃金面前似乎失去了說服力。消費者排隊數小時仍一貨難求,究竟是出于對品牌的認同、對黃金保值的信任,還是被社交媒體放大的集體跟風?從財務數據來看,老鋪黃金的表現堪稱亮眼:2025年上半年營收達123.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51%;毛利率約38.1%,是行業平均水平的1.5倍;凈利率19%,更是同業的三倍。這種增長并非曇花一現——過去兩年,其營收從2023年的30億元躍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123億元,利潤也從不足4億元攀升至近24億元,增速與盈利能力均遠超傳統黃金零售企業。
然而,高利潤是否等同于強品牌?老鋪黃金的定價邏輯與傳統金店截然不同。周大福、老鳳祥等品牌的核心定價模式是“金價+加工費”,消費者購買的是黃金本身的重量與純度,品牌更像是銷售渠道。而老鋪黃金采用“按件計價”的方式,將首飾視為成品而非原料加工品,引導消費者關注設計而非克重。這種模式在金價上漲時顯得尤為巧妙——產品價格固定,金價越高,消費者越覺得“買到即賺到”,從而刺激購買欲望。今年內,老鋪黃金僅調價三次,這種克制策略使其在金價上漲周期中獲得了超額收益。
但這是否意味著老鋪黃金已躋身奢侈品牌行列?答案并不簡單。對奢侈品牌而言,原料價格波動幾乎不影響銷售——消費者不會因黃金漲價而放棄購買卡地亞。以布契拉提、寶曼蘭朵等品牌為例,其產品多非24K足金,消費者購買的是設計、文化與身份認同,而非黃金本身。傳統金店與奢侈品牌的核心分野,在于能否擺脫貴金屬的成本束縛,通過設計、敘事與文化價值重新定義價格。老鋪黃金雖以38.1%的毛利率領跑行業,遠超傳統黃金加工商10%-25%的毛利區間,但其產品原料成本占比仍達30%-65%,顯著高于奢侈品牌單品的10%左右。這表明其定價仍深度依賴黃金價格,尚未建立足夠支撐高溢價的品牌邏輯。
消費者購買老鋪黃金的動機同樣值得玩味。其門店采用“一對一”顧問式服務,提供依云水、圣培露,甚至設有VIP廳,營造出奢侈品牌的購物體驗。但暢銷產品多為素金款手鐲,即以純黃金克重為主的款式。對多數消費者而言,購買素金款并非單純為審美,而是出于“保值安全感”——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黃金的克重是看得見的財富。老鋪黃金的熱銷,反映了消費者在“保值”與“悅己”之間的心理博弈:看似追求設計,實則仍是一次關于安全感的消費。素金款中黃金成本約占售價的60%,而鑲鉆款中黃金占比僅約30%,后者更接近“設計溢價”邏輯。然而,消費者瘋狂搶購的恰恰是品牌附加值最低、與金價波動關聯最強的素金款。
社交平臺上的“老鋪黃金窮人三件套”——克重較小、總價較低的單品——成為熱門話題。這一自嘲式熱詞暴露了消費者的矛盾心態:既渴望奢侈品的儀式感,又在克重與升值邏輯中尋找安全感。這種反差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金價下跌、股價走弱的背景下,老鋪黃金卻在零售端逆勢熱銷,看似脫離了金價邏輯,但暢銷品結構又顯示其仍被金價牽引。老鋪黃金正處于一個微妙的中間狀態:一只腳踩在原料邏輯上,另一只腳已踏向文化敘事。
從產業邏輯看,老鋪黃金若想真正擺脫金價周期的束縛,將定價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似乎只有一條路——向奢侈品牌化轉型。布契拉提、寶曼雅寶等品牌的成功證明,“設計與故事”能讓貴金屬脫離原料邏輯。但這條路也暗藏風險:以西方奢侈品牌的敘事方式包裝東方工藝,可能讓“中國奢侈”始終處于被定義的角色。老鋪黃金的獨特性在于,它既擁有東方手工的文化根基,又具備現代零售的商業邏輯。它尚未成為中國的布契拉提,但也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黃金老鋪”。在全球奢侈品體系之外,中國或許需要一套新的敘事,而老鋪黃金的故事,仍在黃金價格的陰影下延續。其所處的“從克重到符號的過渡”階段,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記錄的時代切片。這家公司用五年時間完成了從黃金加工商到文化品牌的跨越,但能否真正擺脫金價邏輯、走出獨立品牌的估值體系,仍需時間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