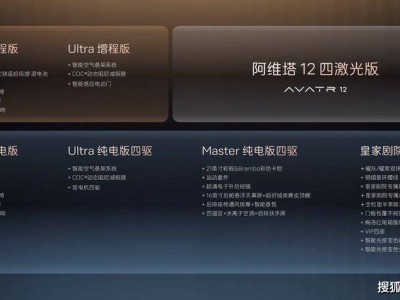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振寧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這位跨越世紀的科學家,用畢生精力在物理學領域刻下深刻印記,也在人生長卷中書寫了學術、友情與愛情的動人篇章。
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的楊振寧,自幼在戰火中成長。少年時代隨家人輾轉逃難,從合肥到昆明,從書桌到防空洞,甚至在抗戰期間目睹租住房屋被炸成廢墟。他仍用鐵鍬從廢墟中挖出幾本幸存的英文書籍,這些書籍成為他與世界對話的最初窗口。在西南聯大求學時,他與黃昆、張守廉并稱“物理三劍客”,筆記本封面上“科學,是信仰的另一種形式”的箴言,折射出他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赴美留學后,楊振寧與物理學大師費米教授結下深厚淵源。兩人在芝加哥大學湖畔討論中微子問題的場景,被費米回憶為“他不是在尋找答案,而是在追趕宇宙本身”。1956年,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顛覆了物理學界對左右對稱性的固有認知。次年,兩人以破紀錄的速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站上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時,楊振寧年僅35歲,李政道31歲。這一理論不僅改變了物理學范式,更讓楊振寧說出“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的感言。
此后,他與米爾斯提出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將局部對稱性原則推廣至非阿貝爾群,成為現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基石。這項理論為多個諾貝爾獎發現提供了理論框架,被戴森評價為“繼愛因斯坦、狄拉克之后20世紀物理的卓越設計”。
在科學探索之外,楊振寧始終是中國物理事業發展的推動者。1971年,他成為首批回國訪問的海外華人學者,從紐約經巴黎輾轉飛抵中國。他積極促成中國高能物理、凝聚態物理與國際接軌,協助建立多個國際水平實驗室。2014年,92歲的他在浙江大學演講時,將自己的人生軌跡比作一個圓:“從一個地方開始,走了很遠的地方,現在又回來了。”
這位科學巨匠也有審慎的一面。2017年,他公開反對中國立即興建耗資巨大的強子對撞機,認為“高能物理的盛宴已過”,投入產出比例不合適。這種基于科學判斷的直言,展現了他對學術責任的深刻理解。
在科學史上,楊振寧的友情軌跡同樣值得銘記。他與李政道的合作曾開啟物理學新紀元,但因理念分歧與署名糾葛,兩人在1962年后再無合作。即便決裂,他仍在公開場合為合作者米爾斯正名,對這段友情裂痕始終抱有遺憾。他的科學生涯中,愛因斯坦、費米、奧本海默、泡利等大師的名字,既在學術上與他交匯,也在思想上與他碰撞。當這些同行者陸續辭世,他常以“不在了”的感慨,流露出科學長路上的孤獨。
愛情為這位理性科學家的生命增添了溫暖底色。1949年圣誕節,他在普林斯頓一家中國餐館與昔日學生杜致禮重逢。這段被楊振寧稱為“命運之神安排”的相遇,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為了每周能坐火車去紐約與杜致禮相見,他決定延長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停留時間。1950年,兩人在普林斯頓教堂完婚,杜致禮此后半個多世紀默默支持他的科研事業,成為他“身后最堅實的支柱”。2003年杜致禮去世后,2004年楊振寧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研究生翁帆再婚,這段年齡相差54歲的婚姻引發社會爭議,但他始終以溫柔態度保護著妻子。
生活中的楊振寧同樣充滿詩意。他與翁帆深夜驅車觀看火山熔巖噴發,妻子生日時挽發換袍唱起昆曲《牡丹亭》,他則含笑靜聽。兩人創立的“楊-翁Studio”里,他親自拍攝、剪輯生活片段并配樂,記錄下旅游、聚會等日常瞬間。
這位跨越世紀的科學家,在事業中以理性丈量宇宙,在友情里與思想者共鳴,在愛情中保有溫柔。他留下的不僅是改變物理學的公式,更是一個科學家在無序人世中保持清醒的生命范本。當歷史的長河繼續流淌,他描繪的公式仍在運轉,而他的故事,已成為科學史上最簡潔的方程——E=科學+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