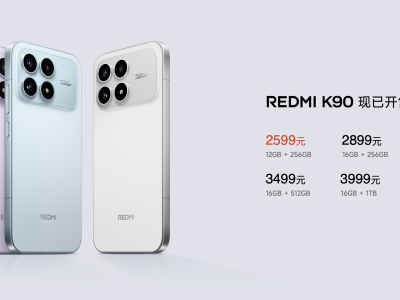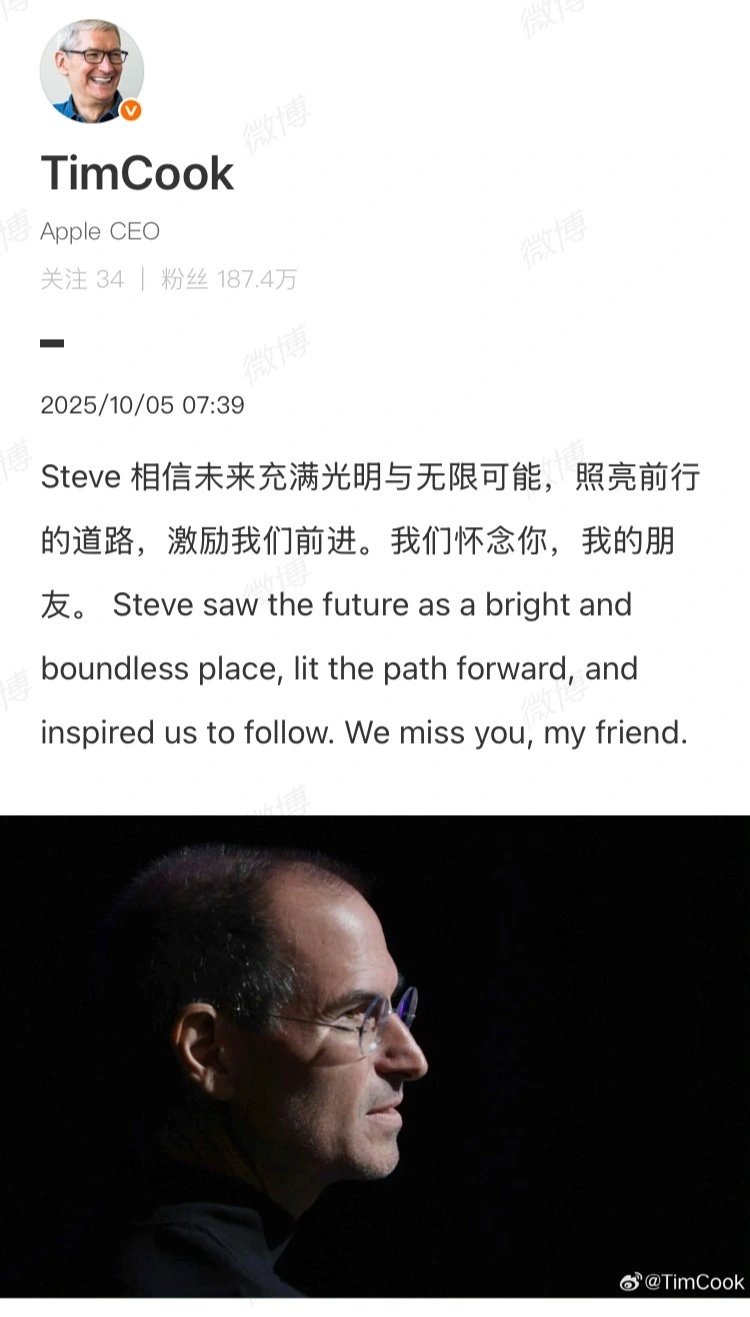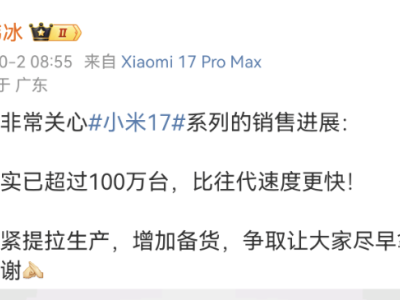美國正經歷一場靜默的飲食革命。外賣服務讓這個國家蛻變為“即時餐飲王國”,消費者只需輕點屏幕,任何時段的任何美食都能精準送達——從深夜的馬提尼到午間的和牛牛排,從法式紅酒燉雞到便利店冰淇淋。這種便利背后,餐飲業的生態鏈已發生根本性改變,傳統餐廳的生存邏輯正被科技平臺重新定義。
2006年,佐治亞理工學院工程系學生科林·華萊士因課堂饑餓突發奇想:能否開發在線訂餐系統?這個源于學生宿舍的創意,最終演變為Grubhub的核心技術。當時的外賣局限于電話訂餐和有限品類,而華萊士的系統首次實現了訂單與餐廳后廚的實時同步。五年后,這項技術隨公司被收購進入主流視野,其發明者也意外成為餐飲科技革命的關鍵推手。
全美餐飲協會數據顯示,2024年餐廳訂單中近75%為外賣或自提,較2019年增長32%。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主要推動力,45歲以下群體中超半數每周至少點一次外賣,13%的人保持每日消費頻率。這種趨勢已突破代際和地域界限:八分之一的嬰兒潮一代與五分之一的農村居民每周使用外賣服務。全球范圍內,DoorDash以38.6億美元收購英國Deliveroo后,新平臺覆蓋40余國,月活用戶達5000萬。
傳統“全服務餐廳”的轉型尤為顯著。這類餐廳的堂食比例已從2019年的70%降至2024年的40%,用餐區在非高峰時段常現空置。行業分析師約瑟夫·波拉克指出,高端餐廳仍堅守堂食體驗,但中端餐飲幾乎全面轉向外賣模式。部分連鎖品牌甚至改造門店結構,紐約長島新開的蘋果蜂餐廳設置整排儲物柜,徹底取消傳統用餐區,將空間效率提升至極致。
這場變革的推手是21世紀初涌現的科技平臺。從1999年的Seamless到2013年的DoorDash,這些企業通過風險投資快速擴張,用補貼策略培養用戶習慣。消費者享受低價美食,餐廳維持利潤,差額由硅谷資本填補。這種模式在2020年疫情期間達到頂峰,主流平臺銷售額一年內翻倍,外賣從“偶爾享受”變為“生存必需”。
但便利的代價逐漸顯現。外賣平臺抽成比例最高達30%,疊加支付手續費、廣告費和優先展示費后,餐廳利潤被大幅壓縮。西海岸餐飲集團經營者香農·奧爾透露,其旗下餐廳2024年外賣收入占比50%,但40萬美元利潤流入平臺,相當于兩份員工薪水。為應對成本,餐廳普遍調整菜單:減少油炸食品,增加燉菜和分裝醬料,甚至出現專為外賣設計的“低工序菜品”。
配送環節的問題同樣突出。平臺算法迫使配送員追求速度而非安全,該職業成為美國高風險工作之一。南卡羅來納州配送員反映,五英里路程僅獲3.5美元報酬,而顧客支付費用達15美元。這種剝削模式隨著行業整合加劇,DoorDash與優步合計控制美國90%市場后,配送員收入進一步下降。
餐廳空間設計也在發生革命性變化。室內設計公司推出“外賣友好型”方案:設置自行車停放區、專用入口和整面墻的儲物柜。但這種混合功能空間引發爭議,設計師勞倫·奇普曼指出,當配送員抱著外賣袋在用餐區穿梭時,傳統用餐體驗必然受損。更極端的是“幽靈廚房”的興起,這些僅提供外賣的餐飲工廠完全取消堂食區域,徹底顛覆餐廳定義。
主廚菲利普·福斯的經歷折射出行業困境。其米其林星級餐廳EL Ideas曾嘗試外賣,但245美元套餐的配送成本使項目難以為繼。“如果將大部分營收交給平臺,整個餐飲業將被摧毀,”福斯表示。如今堅持外賣的餐廳不得不裁員、提價,甚至與分期付款平臺合作,允許顧客分月支付餐費。
這場變革的深層矛盾在于價值重構。傳統餐廳提供的是包含空間、服務與社交體驗的完整產品,而外賣平臺將餐飲簡化為可配送的商品。作家希拉里·迪克斯勒·卡納萬擔憂,當烹飪創新必須適配配送容器時,美食的藝術性將不可避免地退化。芝加哥餐廳經營者湯姆·科利基奧更直言:“外賣平臺本質上在說,不用我們的服務就別想生存。”
作為變革的起點,華萊士如今成為批判者。離開Grubhub后,他反思科技對傳統行業的改造:“我們創造了不存在的需求,再用資本補貼培養依賴,最終讓所有人陷入零和博弈。”這種覺醒源于他對餐廳經營成本的深入了解,當公司討論提高傭金時,他意識到這種模式注定不可持續。現在的華萊士很少點外賣,他希望消費者能意識到,每次輕點屏幕背后,是基礎設施、社區生態和勞動者權益的隱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