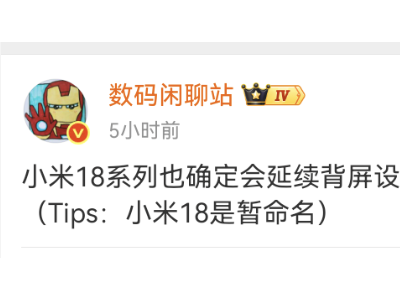中國電商行業進入存量競爭階段,作為頭部企業的阿里巴巴正面臨增長壓力與競爭加劇的雙重考驗。在此背景下,蔣凡的回歸與權力集中,不僅是個體職業軌跡的起伏,更折射出這家互聯網巨頭在戰略方向、組織架構和技術應用層面的深度調整。
從“價值觀至上”到“業務導向優先”的轉變,是阿里巴巴組織邏輯調整的核心特征。2020年,蔣凡因個人事務被取消合伙人身份并調離核心業務,但阿里巴巴并未完全否定其價值,而是將其派往國際數字商業板塊。2025財年,該板塊收入達1323億元,同比增長近三成,成為集團增長最快的業務。這一成績使蔣凡在2024年重返核心管理層,并于2025年進入合伙人委員會,成為最年輕的成員。
這種“起落”背后,是阿里巴巴從強調價值觀純粹性轉向以業務結果為導向的實用主義。2023年9月,吳泳銘出任CEO后推行“年輕人提上來、用起來”的用人原則。蔣凡的回歸正是這一邏輯的體現:他兼具技術背景(曾主導手淘“千人千面”算法)和國內外業務經驗,完美契合阿里巴巴“聚焦電商、AI驅動”的戰略方向。同時,合伙人制度的精簡(從26人減至17人,9位元老退出)進一步強化了組織彈性,使決策更貼近業務一線。
在業務層面,阿里巴巴的競爭維度正從“流量爭奪”轉向“生態協同效率”。2024年11月,阿里巴巴成立電商事業群,由蔣凡統管淘寶、天貓、國際業務、1688、閑魚等板塊;2025年6月,餓了么與飛豬并入該事業群,形成覆蓋實物電商、即時零售、旅行服務的超級平臺。這種整合通過協同效應,將阿里巴巴原有的資源沉淀轉化為結構性優勢。例如,淘寶閃購與餓了么的整合帶來日均8000萬單的訂單量,同時通過高頻消費提升用戶黏性,帶動淘寶DAU大幅增長。
生態協同的關鍵在于構建供給側壁壘。蔣凡通過整合阿里巴巴的供應鏈、物流與數據能力,形成“立體零售網絡”。在近場零售中,淘寶閃購的“閃電倉”已突破5萬家,25%的供給直接來自阿里生態;在遠場電商中,天貓品牌線下門店接入閃購體系,實現“線上下單、門店發貨”。這種整合使阿里巴巴具備任何單一平臺難以復制的優勢:外賣起家的平臺缺乏電商基因,傳統電商平臺則缺乏即時履約網絡。
效率提升是生態協同的終極目標。蔣凡在阿里巴巴內部發起“成本重構”戰役,通過規模效應與科技賦能優化UE(單位經濟模型)。例如,淘寶閃購通過訂單密度提升與客單價增長,單均履約成本顯著下降;AI調度系統將配送時效壓縮至分鐘級,成本大幅降低。這種效率優化不是簡單的補貼戰,而是通過運營升級實現結構性成本優勢。據多家媒體報道,蔣凡預測,未來三年閃購和即時零售將為阿里巴巴帶來1萬億交易增量,其本質是通過生態協同重構人、貨、場的匹配效率。
在技術層面,阿里巴巴正從“業務支持”轉向“AI重構內核”。2025年,阿里巴巴宣布未來三年投入3800億元于AI+云領域,超過過去十年總和。在電商場景中,AI不再僅是優化工具,而是深入供應鏈、物流、用戶體驗等環節,成為業務創新的核心引擎。例如,淘寶基于通義千問大模型推出“淘寶問問”AI助手,能理解復雜購物需求,提供個性化推薦;AI工具“生意管家”幫助商家生成商品描述、分析數據,中小商家推廣成本大幅下降。
AI對供應鏈的重構尤為深刻。阿里巴巴將AI技術應用于全鏈路管理,實現“以銷定產”的精準運營。例如,通過分析歷史銷售數據、季節因素與市場趨勢,AI系統預測商品需求,優化庫存布局,這種技術賦能使阿里巴巴從“交易平臺”升級為“智能零售基礎設施”。技術的深度應用,使阿里巴巴在體驗與效率上構建了差異化優勢。
AI驅動為阿里巴巴打開了第二增長曲線。2025財年,阿里云AI相關產品收入連續多個季度實現大幅增長,云業務占總收入比重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AI技術成為電商業務的核心競爭力。蔣凡在財報中強調,AI驅動不僅提升了用戶體驗,還優化了商家效率,例如“全站推廣”工具幫助商家提高營銷效率。這種技術賦能使阿里巴巴在增長放緩的市場中保持韌性,2025財年淘天集團收入同比增長,扭轉了此前增速停滯的局面。